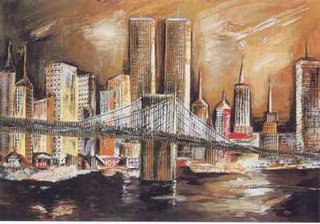星期五, 11月 11, 2005
掌聲響起
今年金馬影展,我照例選了一組數位競賽短片觀賞。原因之一,是喜愛那種實驗性強,能激發想像力的電影,而且保證再怎麼難看也不會一次折磨人數小時;原因之二,是喜愛短而有力的劇情,尤其是一連十幾部,好像吃精緻buffet一樣,便宜大碗。原因之三,也是最主要的原因,則是能享受觀眾的參與和掌聲。
這些競賽片來自世界各地,導演多半很年輕,有些還是電影系學生,有些則是初次嘗試拍動畫的老手。由於一部片子頂多十幾分鐘,可以不用花上很多成本(事實上,很多導演坦承全片都是親友等善心人士贊助的),因此最乖誕、莫名其妙、憤世嫉俗的東西都可能出現。那怕只是導演自己一場夢的再現,或是純粹靠技術傳達一個概念(死、老、自由、反戰等),也都可以被接受發表。同時,為宣揚自己的理念,順便幫自己拉票,導演常常會到場解說他的創作概念,並回答觀眾的問題。
這是我認為最精彩的時刻,觀眾可以在剛剛接受到影片衝擊之後,立刻和創作者對話,拋出各種疑問。也許是質疑、也許是讚許,但絕對不需要抱著揣測回家。於是,我知道了為什麼導演選擇某個色調,原來他希望藉此表現特定的情緒;我知道了導演如何產生靈感製作成故事,原來是因為他有過類似的經驗;我也知道了原來自己有時候想太多、詮釋太多,導演根本沒想過我看完片子後想到的東西。
然後,就是掌聲。去年看競賽片時,是每放完一部短片觀眾就鼓掌一次,今年則是全部放完後大家再鼓掌。雖然不確定導演是否在現場,能否聽到掌聲,但那是都對他人血汗結晶的讚許。不管拍的好不好,觀眾有沒有看懂,那都是最直接向導演、向影片致意的方式:「謝謝你讓我看到一部電影!」想像導演坐在位子上,邊看影片邊回想他經歷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完成的作品,能夠被一群陌生的人觀賞、鼓勵,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刻!而觀眾在鼓掌的當下,似乎也能感受到同在席間的其他觀眾所營造出來的集體力量:大家都來了,都來看電影。
在電影公開放映的歷史上,掌聲一直都很重要。當還是無聲電影的時期,電影院裡多半會請一位「辯士」,擔任電影解說員的角色,隨著劇情起伏而加油添醋。複雜一點的還會找來五人樂隊,悲劇時拉小提琴、喜劇時打鼓。觀眾陶醉在影片的故事和畫面裡,會齊聲大笑,也會一同啜泣。誇張一點的,電影院還可以像遊樂園一樣,小孩嬉戲、情侶說愛(甚至「做」愛,如影片「新天堂樂園」中的橋段)、吃喝配著電影,像看舞台劇似的熱鬧。電影播畢,觀眾一定起身鼓掌。那是一種默契,更是一種儀式。
如今,有太多消耗我們激情的地方,去KTV嘶吼到嗓子啞,流連夜店暢飲狂歡。只不過,社會越來越開放,人卻越來越壓抑,看電影時我們吝於展露情感,難過不敢哭出來怕人笑、開心不敢出聲怕自己出糗。尤其在燈光亮起時,大家一定要裝作沒事的樣子,收拾收拾快快蜂擁而出,深怕多待一刻會被別人看出自己的七情六欲似的。對我而言,電影如文學作品一般,目的是去創造感動的。不能讓你感動的電影或許就稱不上成功,但如果電影讓你感動了,何妨坦然迎接情緒?
至少,給點掌聲吧!給那些幕前幕後、有名無名的電影人,一點尊敬。
今年金馬影展,我照例選了一組數位競賽短片觀賞。原因之一,是喜愛那種實驗性強,能激發想像力的電影,而且保證再怎麼難看也不會一次折磨人數小時;原因之二,是喜愛短而有力的劇情,尤其是一連十幾部,好像吃精緻buffet一樣,便宜大碗。原因之三,也是最主要的原因,則是能享受觀眾的參與和掌聲。
這些競賽片來自世界各地,導演多半很年輕,有些還是電影系學生,有些則是初次嘗試拍動畫的老手。由於一部片子頂多十幾分鐘,可以不用花上很多成本(事實上,很多導演坦承全片都是親友等善心人士贊助的),因此最乖誕、莫名其妙、憤世嫉俗的東西都可能出現。那怕只是導演自己一場夢的再現,或是純粹靠技術傳達一個概念(死、老、自由、反戰等),也都可以被接受發表。同時,為宣揚自己的理念,順便幫自己拉票,導演常常會到場解說他的創作概念,並回答觀眾的問題。
這是我認為最精彩的時刻,觀眾可以在剛剛接受到影片衝擊之後,立刻和創作者對話,拋出各種疑問。也許是質疑、也許是讚許,但絕對不需要抱著揣測回家。於是,我知道了為什麼導演選擇某個色調,原來他希望藉此表現特定的情緒;我知道了導演如何產生靈感製作成故事,原來是因為他有過類似的經驗;我也知道了原來自己有時候想太多、詮釋太多,導演根本沒想過我看完片子後想到的東西。
然後,就是掌聲。去年看競賽片時,是每放完一部短片觀眾就鼓掌一次,今年則是全部放完後大家再鼓掌。雖然不確定導演是否在現場,能否聽到掌聲,但那是都對他人血汗結晶的讚許。不管拍的好不好,觀眾有沒有看懂,那都是最直接向導演、向影片致意的方式:「謝謝你讓我看到一部電影!」想像導演坐在位子上,邊看影片邊回想他經歷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完成的作品,能夠被一群陌生的人觀賞、鼓勵,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刻!而觀眾在鼓掌的當下,似乎也能感受到同在席間的其他觀眾所營造出來的集體力量:大家都來了,都來看電影。
在電影公開放映的歷史上,掌聲一直都很重要。當還是無聲電影的時期,電影院裡多半會請一位「辯士」,擔任電影解說員的角色,隨著劇情起伏而加油添醋。複雜一點的還會找來五人樂隊,悲劇時拉小提琴、喜劇時打鼓。觀眾陶醉在影片的故事和畫面裡,會齊聲大笑,也會一同啜泣。誇張一點的,電影院還可以像遊樂園一樣,小孩嬉戲、情侶說愛(甚至「做」愛,如影片「新天堂樂園」中的橋段)、吃喝配著電影,像看舞台劇似的熱鬧。電影播畢,觀眾一定起身鼓掌。那是一種默契,更是一種儀式。
如今,有太多消耗我們激情的地方,去KTV嘶吼到嗓子啞,流連夜店暢飲狂歡。只不過,社會越來越開放,人卻越來越壓抑,看電影時我們吝於展露情感,難過不敢哭出來怕人笑、開心不敢出聲怕自己出糗。尤其在燈光亮起時,大家一定要裝作沒事的樣子,收拾收拾快快蜂擁而出,深怕多待一刻會被別人看出自己的七情六欲似的。對我而言,電影如文學作品一般,目的是去創造感動的。不能讓你感動的電影或許就稱不上成功,但如果電影讓你感動了,何妨坦然迎接情緒?
至少,給點掌聲吧!給那些幕前幕後、有名無名的電影人,一點尊敬。
星期四, 11月 10, 2005
此一時、彼一時的鄉愁
一九八八年,紐約還是一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城市,人們還在適應曼哈頓摩天樓的壓迫,窄小的巷弄和寬敞的大道並存,全世界的移民爭相湧入。
其中,最顯眼的是那些避過歐陸大戰烽火、納粹屠殺的猶太人。他們主要來自最早被德國攻陷的波蘭,那兒的村莊被燒毀、村民被凌辱或送入集中營,父母用僅剩的力量將稚齡子女送往美國,期許他們在那兒重生。帶著吉普賽人的神秘靈氣,他們在陌生的美國建造起猶太教堂(synagogue),閱讀猶太經文「塔木德」(Talmud),自成哀傷而充滿鄉愁的一群。
這是影片「美國故事」(American Stories, Food, Family, Philosophy) (1988)的背景,為比利時生、現旅居法國的女紀錄片名導香妲艾克曼(Chantal Akerman)早年的作品。艾克曼算是法國新浪潮後期的前衛導演,她的電影主題多半環繞著身份認同、女性意識和政治打轉。她因為以尖酸的幽默、解構主義式的風格直接衝撞主流意識型態,而被紐約時報譽為影史上女性電影第一人(the first masterpiece of the feminine in the history of cinema”)。
影片中,艾克曼大量運用獨白方式,讓當事人(或演員)述說一則則思念、排拒、害怕、無助的波蘭移民故事。有些人絕望欲死、有些人未死而新生,還有更多飄盪的沒有身份、沒有明天的人。透過無殼、不知道在等待什麼、找不到路等隱喻,艾克曼直指移民的普遍徬徨。即便擁有穩定的工作、兒女成群的家,這群移民第一代依舊忐忑:他們不認識自己養育長大的「美國小孩」,對他們來說,第二代對祖國波蘭的失語、失憶,深深刺痛這些吸吮遙遠波蘭奶水的老一輩。而那些尚未婚嫁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,他們恐懼自己對他人的愛(無法抗拒又無法接受)、背負不可告人的秘密(譬如曾被強暴的記憶)、不知道是否能愛「外邦人」(非猶太人)。他們沒了父母,凡事只能靠自己體會、自己經驗。在偌大的紐約,他們失了根卻擺脫不掉鄉愁。
艾克曼層層剖析不同情境下同樣的移民者的心情,那是歷史太多、太沈重的後遺症,放不下的事情好像很多,但仔細想來卻已經模模糊糊,宛如影片舞台劇似的明滅燈光,又宛如影片初始的一段話:當子孫已經遺忘先人禱告的地點、禱告的儀式、禱告的內容時,只剩下一顆虔敬的心,不清楚前世何來和今生何去。移民的宿命啊…
我不頂愛這部電影。太多突兀的對話,當下看了笑一笑也罷,但不太能像潮水般將我淹沒。但話說回來,此片單薄的形式,可能也代表了移民生活的蒼白空洞(還是說我其實高估了艾克曼?)。連副標題「食物、家庭、哲學」,在片中也被當成泡妞的伎倆,真是夠了。
鄉愁啊~鄉愁,多少人因汝之名而生、而死。身為外省第三代的我,只是一個前不知古人的來者,和那些二十年前在紐約市掙扎過的波蘭移民微微的心靈相通著。只是八零年代的鄉愁,和現在的鄉愁或許已經全然不同。艾克曼沒有說的是,這些移民如何被捲入新的政治遊戲裡,面對原居者又存在多少語言、習慣、心靈的距離。活在紛擾的台灣,某些體會可能比艾克曼能講的多一些、深一點;因此,覺得她的論述不足,也因此,不喜歡這部電影,可以嗎?
一九八八年,紐約還是一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城市,人們還在適應曼哈頓摩天樓的壓迫,窄小的巷弄和寬敞的大道並存,全世界的移民爭相湧入。
其中,最顯眼的是那些避過歐陸大戰烽火、納粹屠殺的猶太人。他們主要來自最早被德國攻陷的波蘭,那兒的村莊被燒毀、村民被凌辱或送入集中營,父母用僅剩的力量將稚齡子女送往美國,期許他們在那兒重生。帶著吉普賽人的神秘靈氣,他們在陌生的美國建造起猶太教堂(synagogue),閱讀猶太經文「塔木德」(Talmud),自成哀傷而充滿鄉愁的一群。
這是影片「美國故事」(American Stories, Food, Family, Philosophy) (1988)的背景,為比利時生、現旅居法國的女紀錄片名導香妲艾克曼(Chantal Akerman)早年的作品。艾克曼算是法國新浪潮後期的前衛導演,她的電影主題多半環繞著身份認同、女性意識和政治打轉。她因為以尖酸的幽默、解構主義式的風格直接衝撞主流意識型態,而被紐約時報譽為影史上女性電影第一人(the first masterpiece of the feminine in the history of cinema”)。
影片中,艾克曼大量運用獨白方式,讓當事人(或演員)述說一則則思念、排拒、害怕、無助的波蘭移民故事。有些人絕望欲死、有些人未死而新生,還有更多飄盪的沒有身份、沒有明天的人。透過無殼、不知道在等待什麼、找不到路等隱喻,艾克曼直指移民的普遍徬徨。即便擁有穩定的工作、兒女成群的家,這群移民第一代依舊忐忑:他們不認識自己養育長大的「美國小孩」,對他們來說,第二代對祖國波蘭的失語、失憶,深深刺痛這些吸吮遙遠波蘭奶水的老一輩。而那些尚未婚嫁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,他們恐懼自己對他人的愛(無法抗拒又無法接受)、背負不可告人的秘密(譬如曾被強暴的記憶)、不知道是否能愛「外邦人」(非猶太人)。他們沒了父母,凡事只能靠自己體會、自己經驗。在偌大的紐約,他們失了根卻擺脫不掉鄉愁。
艾克曼層層剖析不同情境下同樣的移民者的心情,那是歷史太多、太沈重的後遺症,放不下的事情好像很多,但仔細想來卻已經模模糊糊,宛如影片舞台劇似的明滅燈光,又宛如影片初始的一段話:當子孫已經遺忘先人禱告的地點、禱告的儀式、禱告的內容時,只剩下一顆虔敬的心,不清楚前世何來和今生何去。移民的宿命啊…
我不頂愛這部電影。太多突兀的對話,當下看了笑一笑也罷,但不太能像潮水般將我淹沒。但話說回來,此片單薄的形式,可能也代表了移民生活的蒼白空洞(還是說我其實高估了艾克曼?)。連副標題「食物、家庭、哲學」,在片中也被當成泡妞的伎倆,真是夠了。
鄉愁啊~鄉愁,多少人因汝之名而生、而死。身為外省第三代的我,只是一個前不知古人的來者,和那些二十年前在紐約市掙扎過的波蘭移民微微的心靈相通著。只是八零年代的鄉愁,和現在的鄉愁或許已經全然不同。艾克曼沒有說的是,這些移民如何被捲入新的政治遊戲裡,面對原居者又存在多少語言、習慣、心靈的距離。活在紛擾的台灣,某些體會可能比艾克曼能講的多一些、深一點;因此,覺得她的論述不足,也因此,不喜歡這部電影,可以嗎?